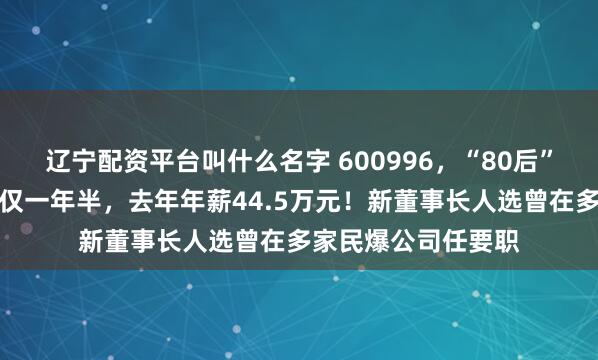1971年10月,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的那一晚,纽约街头秋风猎猎。自此以后,北京的外交节奏明显加速,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道加急电报飞往各国使馆配资炒股大全,叮嘱“大事在前,务必慎重”。两年后,一场意想不到的失误打破了外交系统一贯的严密——地点在地中海东岸的希腊。
事情真正的导火索并不复杂,却离奇得像电影桥段。1973年5月7日上午,我驻希腊使馆里依旧例行忙碌:值班官员登记来往电报,翻译核对晚宴名单,谁也没料到,一张日期、国别都被误读的请柬即将引爆“雅典风波”。那天中午,大使周伯萍刚从希腊外交部洽谈完访问事宜,正打算回馆换身正装。临出车门,随行翻译匆忙通报:“科威特国庆招待会只剩十来分钟,我们得立刻赶过去。”时间紧、路况乱,加之希腊警车本就爱扎堆,大使信以为真,当即调头。
警车的引导灯闪个不停,周伯萍的座车很快驶入一幢崭新的两层白楼。门口站着的外交官衣着笔挺,谁能想到这其实是以色列驻希腊代表处。短短十几秒握手寒暄,被蹲守的美国记者抓了个正着,快门声清脆——整个误会就此定格。第二天,美国报纸标题耸人听闻:“中国大使祝贺以色列国庆,北京是否改变中东政策?”

报纸送到雅典各使馆时,周伯萍正在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参加真正的国庆招待会。同席的罗马尼亚大使凑过来,小声提醒:“周大使,外电说你昨天去了以色列代表处,出什么状况了?”这一句点醒梦中人。周伯萍脸色骤变,立刻离席回馆调取请柬。那张请柬上清清楚楚写着“5月8日,捷克斯洛伐克国庆”,而署名的“Kovik”竟被值班人员当成了“Kuwait”,日期也被当作7日。两处误读,导致大使误入“禁区”,当真祸从天降。
最尴尬的并不是误入使馆本身,而是当时中国尚未与以色列建交,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高度敏感。希腊媒体、美国媒体迅速放大报道,一时间各种猜测四起。外交部收到紧急电报后,马上将情况陈报北京,并责令周伯萍拟定补救方案。短短几个小时,大使就写出了三条措施:一、向希腊外交部及阿拉伯驻希腊使节当面澄清;二、向国内提交书面检讨;三、在馆内通报,整顿内部流程。
5月14日清晨,法国航空的波音客机落地首都机场。周伯萍走下舷梯,神情凝重。这边,外交部已把事故经过连同补救建议送到中南海。那时,周恩来刚做完膀胱手术不到半个月,本应静养,却借着输液间隙翻阅文件。读到“误祝以色列国庆”几个黑体字,他气得把文件往桌上一拍:“周门不幸!”声调之高,把值班秘书都吓了一跳。长期温文尔雅的总理难得动怒,可见事关重大。
国务院办公会上,周恩来认定这是建国以来性质最恶劣的外交事故之一,点名批评使馆管理松懈。文件很快呈送至毛主席桌前。毛主席审阅后却改了三笔:删去“极为荒唐”字样,改成“因缺少调查研究而误入”;把“较好”检讨态度改为“很好”;最后写一句批示:“同志犯错,治病救人。”几行字,口气缓和不少。
主席的态度直接影响定性。外交部随后降低了处罚等级,对周伯萍作调离处理,任命其为驻阿尔及利亚大使。对外公开口径则强调“个别工作人员失误,不影响中国对中东一贯立场”。阿拉伯兄弟听完解释,没有进一步追责,以色列方面倒是沉默不语——他们心知肚明,这是场显微镜级的乌龙。
回头看,这起风波与其说源自个人疏忽,不如说暴露了当时某些基层环节的粗放管理:文件核对缺少双人复审,翻译刚学英语便值班,紧急应对流程模糊。事故之后,外交部迅速出台编号为“七三条令”的内部通知,要求驻外使馆所有请柬、电报、礼宾表格必须两级复核并签字备案。条令至今仍在沿用,后来被行内人戏称“雅典防错法”。
有人问,为什么毛主席要出手“降温”?原因颇多。首先,1973年中东局势复杂,中国刚打开与阿拉伯国家经贸渠道,倘若把罪名定得过重,易被外界误读成内部分歧。其次,周恩来重病在身,连夜处理此事已是极限;主席的修改,相当于分担压力。再者,大使毕竟主动认错,补救措施妥当,杀鸡儆猴即可。

“外交无小事”这句训诫在风波后传遍各馆。雅典的那间小小会客室,后来换了新地毯,旗杆位置也微调,但墙上的值班记录本一直被保留下来,封面写着“1973年”,提醒后任:任何一个日期、一个字母都关系国家声誉,不容半点侥幸。若非当年毛主席以“治病救人”为原则轻轻一笔,周伯萍的职业生涯恐怕早已画上句号,连带希腊方向的工作也将中断。
几十年过去,“雅典事件”在外交学院课堂上仍被当成案例详解,学生们听完总要感叹一句:纸面错误虽小,后果却能撬动国际关系的齿轮。试想一下,若当时阿拉伯媒体跟进炒作,苏联又插上一脚,中东局势会生出多少枝节?正因危险与机遇并存,决策层才要把事故扼杀在摇篮。

对于70年代奔走世界的中国外交官而言,既要破浪,也要避礁。避免下一次雅典式失误,比任何慷慨陈词都实际。
2
超牛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